升初
刀子警告,be警告,人设崩塌警告,灵感来源loft上看到的一句话,我不是刀子精,我只是键盘的搬运工。
车站雨夜,黄衣女子俨然将发盘起,喜爱粉色,渴望爱情的少女,如今已是少妇之姿,身旁的行李箱任凭凄风冷雨,能为她披上外套,遮蔽寒冷之人,远观伞下,宛若雕岩屹立不前,虽回寒倒冷思绪万千,却只能远望佳人,将欲行之念悉数按下。
远处脚步袭来,稳健之余不急不缓,即使不见表情,伞下人亦能读懂她周身的落寞,来的是荣升,杨慕初最为敬重之人,他将女子揽入怀中,替杨慕初掩去了她的凉意,也给女子带了最后一根稻草,最后一份绝望。
荣升看见他了,杨慕初身着风衣,一副军人的模样,他是他惨死胞弟活着的衣冠冢,是能够证明杨慕次存在过的最后一抹印记。
杨慕初也曾伪装过胞弟,为其所谓的任务打掩护,那时,荣升没有认出他;胞弟曾假披他的衣裳,送荣升回家,在荣华的掩护之下,荣升亦不能分辨一二。可这次他清晰的感受到,荣升认出他了,他是有些无措的,他明白他破了荣升的规矩。他看得出荣升眼中一瞬的怒意,最终却也是化作一片叹息,淹没黑暗。
那份叹息杨慕初是认识的,他想起几月前,他初得爱人,欣喜若狂,跑到荣升的身边颇有嘚瑟之意,荣升似往日般不冷不热直泼人冷水,之后却触景伤情,想起自己已故的妻子,最后的长叹同今日如出一辙。
“爱她,就好好珍惜她,有时候就如你所言,明知道她就在那里,但你却一动也动不了……”
“你是身在局外不知其味呀,如果某个突发事件,让你放弃你所拥有的爱情……你做不到……”
荣升于杨慕初而言是兄长,是主人亦是老师,虽也有过诸多不满,但杨慕初不得不承认,这位少爷算是个大隐隐于市的智者,他从不张扬,自妻子亡故便更是将那份清明藏于心底,他看似冷漠,迂腐,逃避世事,对于阿初他却为兄为父,赠与了阿初一轮旭日东升。
伦敦的夏季温暖明媚,一年中最暖和的季节,终于让荣初不用将自己裹上几件衣服,出门都感到手脚不便,他刚从图书馆中走出来,充分准备几个月后的考试,争取得到跟赫尔曼教授进修的权利,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脸上常挂着和煦的笑容,一身颇为得体的西装裹身,没了厚衫的束缚,少年健步如飞。
总有国外的姑娘会惦记这样的青年,这个年纪的少男少女,在爱情诗歌的影响下,总期待着一场罗密欧朱丽叶一般的爱情,甚至会遗忘,这实际上是一场彻底的悲剧,或许是金发碧眼的人物看的太多,学校里的姑娘们,倒是对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更多了几分好感,荣初在学校里的人气格外高,夏跃春对此常常感叹,姑娘们人美眼瞎,喜欢这样不识趣的柳下惠。
并非荣初是坐怀不乱真君子,对于一个一心学术和应付金融考试的人而言,现在去感受比翼连枝,如胶似漆实在白费光阴,再者而言,他清楚自己早晚得回国,现如今去祸害人家姑娘,实在是荣初不愿去做的。
看着眼前的病检分析报告,荣初的眼中全是专注,他是一路看着报告过来的,坐到咖啡馆中随意点了杯咖啡,就又投入到了一项项在外人看来颇为头大的数据中去了。
下午阳光正好,将整个咖啡馆照的亮堂宽阔,店员方才浇了水,娇嫩的花叶闪闪发光,叶上一光亮缓缓滑落,滴到地上,荣初长舒了一气,微蹙的眉头这才松开,他满意的将报告压倒最下面,再低头却不由有些苦大仇深起来。
是了,快到期末了,少爷为逃避家族责任硬给自己压上的金融课的考试也该到了。他也不是学不下去,只是私心里不大喜欢,即使对他而言算不上困难,这份课程终究也就变成了一笔负担,他有些苦巴巴的叹了口气,认命的开始看这些恼人的资料,才看上两行就有些分神,抬起咖啡喝上一口,又看了看街上,默默抱怨几句某位损友怎么还没到,将身子一靠,再翘一个二郎腿,看着手里的资料,整个人都失了几分光彩。
“你把资料瞪穿了,你也还得考试!”夏跃春刚进来就看见荣初一脸世界末日的表情,他也知道荣初学金融的特殊性,但总是乐此不疲的用来打趣他,把荣初噎的说不出话,对他而言也是个非常不错的乐趣。
光听声音荣初就知道,这张刻薄到老的嘴的主人是谁了,挣扎着又看了两眼资料,颇觉头大,急急忙忙将它放下,顺便给了夏跃春一个大白眼,不客气的回敬他:“你可真会安慰人。”
夏跃春也不恼,慢条斯理的跟服务员要了咖啡,才又笑着与人斗嘴:“比不上你会自我安慰,”他朝人一抬下巴,意指被荣初暂且放弃在桌上的金融资料“我们荣大学士,在院里可是出了名的好学,手握两大经济命脉,一边救人,一边算着把人家银行里的钱赚出来……”
不等夏跃春说完,荣初就不由举手投降了“行了行了,你越说越夸张,你刻薄成这样,以后当心找不到老婆!”
夏跃春听了这话,更是夸张的叫了起来:“对对对,说起老婆,你不提我差点忘了!”他从自己的包里面翻出了两张信封,一把拍在荣初的面前“荣大学士,快来看看,这里面哪个是你未来的老婆?”
荣初看着这两张散着香水味的信封,更是头大起来,猛的把眼睛闭上捏着眉间哼哼起来“诶呀,嘶……我看来得缓缓,刚才看金融复习资料看的我头痛,你快帮我拿开。”
对面的损友对荣初的态度颇为鄙视,翻着白眼的将信封拿走,嘴上又开始不饶人了“我真是头一次见你这样的人,老婆都要别人拿走的。”
“你又不是不知道,现在我找姑娘,我大哥不得扒了我的皮。”荣初患者在信封拿走后马上就康复了,夏跃春的咖啡刚刚上桌,荣初就毫不客气的在他咖啡里丢了三块方糖,任凭夏跃春嚷嚷着,他不爱喝这么甜的。
终于略占上风的荣初笑着朝人挑眉,“喝点甜的没坏处,特别对你,多喝点能治治你的嘴。”
夏跃春看着迅速化掉的方糖有些哭笑不得,只得用小勺搅拌均匀些,让咖啡不要甜的太过诡异“我告诉你,我手上可有你的罪证。”
“什么?”
“一会儿我就把这两封信送给你大哥去,告你一个先斩后奏偷心贼不负责的罪!”
荣初不由笑出了声,假意告饶“那还请夏大医生高抬贵手,要是我出什么事了,下辈子我还和你做朋友。”
二人笑作一团,夏跃春连连感叹,说荣初太狠,又互相拆台了好一阵,两人才停下闹腾,这会儿夏跃春喝了口咖啡,又颇为嫌弃的放下,才又问起荣初:“下午有什么安排吗?”
“怎么,你有事?”
“下午我有一个会要参加,要是你没什么事的话,陪我去看看,正好你也紧张了好长时间,去放松一下心情。”
夏跃春太过正经,荣初总觉得事情有点不大对,警惕起来了,“什么会能劳动你夏越春去?”
夏跃春笑笑,高深莫测般的推了推自己的眼镜:“学着救人的会,你去不去?”
荣初有些奇怪,大家都是医学院里的学生,有什么救人的手段是我们没学过的?怎么还要专门去听?学院里也没听说最近有什么医学讲座,莫非是外面骗人的讲座?
“什么专题的?你可别被别人骗了。”荣初好心提醒。
夏跃春有些无奈,却也一时不好解释,只得打着哈哈的回答“你就当是医学讲座吧,是不是什么新思想,得去了才知道呀,怎么荣大学士不愿意赏光?”
看着损友一副不依不饶的劲,荣初只得点头答应,本来下午也和少爷说的是去图书馆温书,少一下午,还是去听医学讲座,想来少爷也不会介意的。
二人吃过午饭,就赶往‘医学讲座’的地方,本想着应该不远,荣初却在他们坐车出了闹市区,一路越过泰晤士河,最后到达少人多岔道的旧肯特路的时候,怀疑夏跃春是打算把自己卖给别人做医学解剖材料,他有些担忧的看着好友,站在原地不再走动,盯的夏跃春发毛。
“你是不是借了英国黑帮的钱还不起了,骗我来抵债的?”
夏跃春折服了,他对荣初的想象力给予了高度反击:“哦,是你大哥让我拿你抵债的。走吧,认命吧。”
此时此刻,内心躁动的荣初:“……我上辈子肯定抢你老婆了,这辈子和你做朋友。”
随着他们走的路越发隐秘,他更是怀疑起来,夏跃春走的路,脱离了他,荣初根本走不出来,但越往深处走,人越多了起来,荣初这才稍微放了心,所谓的‘医学讲座’是在一间并不大的房间中,荣初不明白为什么要躲到这样的地方来,若不是有畏光的材料,就只能是什么邪教组织的聚首。
来的人五花八门,有穿着整齐,气质高傲的富家公子,有和他们一样的学生,也有衣衫褴褛,明显已经过的不景气的流浪汉,年纪上更是跨度广泛,襁褓中的婴儿到五六十的老汉,应有尽有,多人挤在这样的空间中,各种气味纷杂,虽说荣初的个子并不算矮,但是也不由有些缺氧的感觉。
人声躁动许久,直至台上上了人,才逐渐安静下来,昏暗的灯泡散发着热量,企鹅一般拥挤的场面更加燥热。
今夜的伦敦是看不见星星的,本就湿润的空气中又多了几分燥热,微微吹过的风却带着丝丝凉意,云层聚集,今夜应该少不了一场大雨。
待荣初好不容易从旧肯特路回到他们住的公寓时,天已经黑了,这场‘医学讲座’花了不少时间,出来后夏跃春曾试探过他的感受,荣初其实是说不上来的,他斟酌片刻,只朝好友一笑,敷衍几句蛮有道理的,便打了岔去谈别的话题了,即使如此,他也看得见夏跃春眼里有和那颗灯泡一样的光亮。
荣初将自己的西装挂在门口的衣架上,大概看了看家中的样子,便直接去了少爷的书房,敲了门得人允许后才进去了。
荣升在画画,这是荣初不用想都能知道的,荣升的袖子已经卷了上去,不算结实的胳膊一手抬着画板,一手拿着画笔,整个人是一副沉浸式的忧郁,他此时此刻画的是蝴蝶,还是蝴蝶。墙角靠着的是刚下了线稿的人像,这副人像,荣升已经画了很多年了,每每提笔都只能画上几笔,便痛苦不堪,再下不去手,唯有蝴蝶似乎是他所能思念亡妻的另一形式,林林总总画了扔,扔了画,他怎么也画不出他满意的样子。
“今天回来的挺晚呀。”荣升退后几步远远的看了看自己画的蝴蝶,不大满意的摇摇头,又提笔接着画,一眼都没看荣初。
“少爷,下午跃春和我去听了一个医学讲座,地址有些偏,所以才回来晚了,今晚您吃了吗?”荣初恭敬的回话,他有些紧张的拾腾起荣升桌上的书,将有些凌乱的书桌规划整齐。
“哦,已经吃过了。”荣升醉心于画中蝴蝶,他是个绝对的浪漫主义,对于理想化的追求太甚,若不是现实生活中总有需要烦扰的事情,他倒是希望自己能逍遥自在。
“我记得,我给你报的金融课,快结业考试了,你准备的怎么样?”
一提这个荣初不免有些无奈,他有些抱怨的朝人开口:“少爷……”
“叫我也没用,别的也就罢了,要是这科你不能好好学,别怪我收拾你。”荣升对于阿初的学业是格外放心的,这孩子聪明,学起东西来远比自己学的快,为了荣家未来的发展,家里一共就两个男丁,自己不愿意总归得有人替自己去做。
“知道了……”荣初嫣了吧唧的翻着荣升桌上刚刚被他放好的书,嘴里不由嘟囔起来:“赶鸭子上架……”
“嗯?”荣升听见了,也不恼,他也清楚阿初只是抱怨几声,该做的他还是会做,但还是忍不住去逗他“说什么呢?”
“没什么,我说,我会好好准备考试的……”拖沓的回话,其中怨念不言而喻,“哦,对了,少爷,你吃饭了没?”
“吃过了。”荣升不由看了荣初一眼,只觉得最近这孩子是不是学傻了。
荣初看着荣升画的蝴蝶,半晌才开口:“少爷,您的画最近越发精进了。”
荣升有些奇怪的看了又看,怎么看也不觉得那里是值得满意的,吸了一口气“是吗?我怎么没看出来?”
“您天天看,肯定看不出来,画了这么多蝴蝶,在配色上,您已经不知道比一开始强了多少了。”荣初讨好的从后面点了点荣升乱七八糟的调色盘。
“怎么?想学了?”荣升有些好笑,什么配色,分明是胡说八道的恭维,这个阿初……
“没没没!少爷您可可怜可怜阿初吧,学业繁重,金融难学的,要是再学个画,阿初可就累死了!”荣初可怜巴巴的嚷嚷起来,之前荣升也不是没动过这样的念头,要不是阿初极力反对,也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个机会去学自己喜欢的医学。
“啧,”荣升有些烦起来,嫌弃起某人在这里打扰自己作画,于是放下了画笔,意思性的打了荣初的胳膊一下,荣初急急忙忙的跳到一边去,“没什么就去多看看考试内容,别在这儿碍眼,打扰我作画。”
“好好好,我走……”荣初揉着自己的胳膊,朝门外走“少爷整天都窝在屋子里,真不怕长蘑菇了?”到了门口还又贫了句嘴。
“阿初!”
“没事,没事,那个,少爷,您吃了吗?”
荣升叹了口气,无奈起来了,接着画画,但到底还是意识到有问题了“说吧,什么事?”
荣初干巴巴的笑了两声,凑了过去“少爷英明,我今日看到有失业的民众游行了。”
“游行?我怎么不知道?”荣升并不关心。
“刚开始一会儿就被英国卫队镇压了,所以没什么消息,只是我刚好看见了,我觉得他们挺可怜的……”荣初将手背在身后,手指玩弄起了自己的袖扣。
“你怎么关心起这事了?怎么?游行队里面有你认识的人?”荣升正画到一个细节部分,站姿都逐渐诡异起来,明显没有关注荣初的意思。
“不是,只是听了他们的口号,对政府的抗议,想要更好的保障,养家糊口。不由有些同情了……”
“凡可說的,皆无意义。凡有意义的,皆不得不以荒唐的语言传递其意义。”荣升以为,阿初这是联想到他自己身上了,所以难免胡思乱想,于是稍微引维特根斯坦的话开导两句。
“我今天去听医学讲座的时候,听到了一种观点,我觉得挺有道理的。”荣初站的愈发端正起来。
“什么观点?”
“医学有时候救的了病人,却救不了所有人,人心难医,资本之心更难照拂大众……”荣升的笔稍微顿了顿,荣初微微颔首,咽了咽口水才又开口“少爷,您觉得马克思怎么样?”
荣升的画笔一滑,一块蝴蝶翅膀的色斑上,平白多了一点其他的颜色,荣升的手有些抖,他暂且放下了画笔,眼睛死死的盯着荣初。
“今天下午,你去听的是什么?”
“少,少爷……”虽有心里准备,但荣初还是有些心虚起来,他挣扎着开口就像夏跃春骗他去一般,却底气全无“只是一个医学讲座……”
“跪下……”荣升深吸了一口气,他感到自己的呼吸都有些颤抖。
“少爷,真的只是个……”
“跪下!”
荣初尚想分辩一二,却被荣升突然爆发的情绪吓的浑身一颤,他有些后悔自己的这番试探,但也知无法挽回,平白为自己找了不痛快,他只楞了一瞬,身体便已经听话的滑了下去,他的手有些发软,却也只是跪的笔直,不敢多言一二。
荣升一时有些难以自控,他大口大口的吸气,试图将自己的情绪稳住,再开口的时,却还是抑制不住自己声音的颤抖“你,你说,今天,下午你去了哪里……”
荣初张了张嘴,最终失去了撒谎的勇气,但终究开始避重就轻起来“我去了旧肯特路……”
荣升现在还耐着性子,他不想自己在暴怒的时候教训阿初“去哪里做了什么?”
“跃春说,那只是一个医学讲座。”荣初低着头,心跳已然失去了控制,在胸膛中快速顶撞,身体也逐渐开始发冷,有些不受控的微微颤抖。
荣升冷冷的看着荣初,现在他已算是出离愤怒,他四处看了看,拿起花瓶中的鸡毛掸子,就冲着荣初的后背抽了几下。
空气中唰唰的声音,听的荣初胆寒,鸡毛掸子上身的滋味实在不好受,背后立马火辣辣的燃起一片,他明白这是少爷的警告,又或者说着已经不止是警告了。
“那,是一个共产党扩员会,为的是召集英国失业人员,与苏联取得联系……”他最终还是说了,却也是说不下去了,他知道荣升理解,只是他不知道,荣升的立场究竟如何。
荣升在荣初身后将鸡毛掸子的一侧点在他的肩膀上“你听了,怎么想?”
荣初的拳头捏了起来,他还在猜,他在猜荣升的态度,他不确定自己的想法是否能让荣升接受,事情已然到了这个地步,那么也没什么好怕了。
他壮了胆子,将问题反问回去:“少爷,又怎么想?”
“唰啪!”
这一下几乎贴着荣初的耳朵,砸在了他的肩上,肩上肉薄,他几乎整条胳膊都卸了力,只闷哼一声,疼的五官都皱了起来。
“回话。”荣升终于在荣初的顶撞下了冷静了下来,他感受到了这个孩子的试探,实话说他有些心寒,他宁愿荣初坦坦荡荡的告诉他自己的想法,哪怕是他不能接受的,他也不至于非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谈话。
荣初的另外一只手死死的捏紧了自己的衣服,才止住了想要去揉一揉肩膀的冲动,他调整着呼吸自以为知晓了荣升的想法,这才小声开口:“回少爷话,阿初先前只是好奇,但并无与他们同流合污的想法,阿初……呃!”
又是一下带着风的击打砸在了荣初的肩膀上,打断了荣初的话,“好,阿初少爷这是不打算好好说话了,”荣升气急反笑,抬脚踹了踹荣初的腿,鸡毛掸子指向方才被阿初收拾整齐的书桌“过去,褪裤。”
荣初瞬时抗拒起来,他几乎马上转身抓住了荣升的裤管,哀求起来:“少爷,阿初错了,阿初不该自作聪明,阿初会好好说话的,少爷!”
荣升低头看着满脸哀求的青年,却不曾心软,平日里他耍些小聪明,荣升都是默许的,今日之事若不是荣初几次三番压在他的底线上,他也不至于如此。
于是他握上荣初的手,将他往前拽了些,手上的掸子就不分地方的朝人身后连抽数下,直打的荣初痛呼出声向前扑倒。再冷冷的举起掸子指向书桌“过去。”
数下连打,余威高存,他知道今晚必然不能再违背少爷哪怕一句话了,他颤抖着从地上爬起来,足下灌铅一般的走至桌旁,将中间的位置略微收拾了出来,抖着手将腰间的皮带解开,放至一旁,连底裤也拉至脚踝处堆积,规矩的俯身,将腿分开,眼眶已经红了起来,他稳住声音开口,终是掩不住惧意“是阿初犯了规矩,请少爷责罚。”
荣升在原地活动了几下手腕,就朝荣初走过去,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声音,也让荣初不由的闭了眼。
竹制的掸子压在臀峰,轻轻拍了几下“委屈吗?”
“阿初,不敢……啊!”
“嗖啪!嗖啪!嗖啪!”
一连三下贴至一处,皮肤被抽打的一阵发白,继而鼓起了一道红的发紫的棱子,掸子抽过的尾部已经微微泛青了。荣初被几次三番的责打逼的几乎不会说话,微微吸着凉气,似乎这般便可缓解身后的疼痛。
“到底是鄙人小看了阿初少爷,今晚上阿初少爷可真是没说上几句实话呀!”假若荣升这般说话,荣初便明白今日不善,如此他还怎敢再言白话,只得低低开口:“委屈。”
掸子挪了地方,又是三下排着向下甩,三条红肿和荣初压抑的痛呼同时在屋中响起。
“那烦请阿初少爷说说,为什么委屈?”
荣初不说话了,他不知该如何开口,是说自己顺着荣升的话说却还是挨打了?还是该说自己并非主动去,是被夏跃春带着去才生出有意参与的想法的?
见人不回复荣升也就没了耐心,抬手便一下接一下的往下抽,将青年白皙的臀部抽出一道道红横,将教训实实在在的刻在肉中。
“撒谎,试我,自作聪明!那一条冤了你?”
掸子次次带风,干燥的竹条不至于伤肉,其韧度也实在够给受罚者一次结结实实的疼痛了。
荣初在桌上早已撑不住责打,整个人趴俯在桌上,腰已经止不住的来回躲闪却怎么也躲不掉哪怕一下责打,身后每挨一下都仿佛皮肉被割了一下,随着掸子的叠加,更像是滚油泼皮一般,一阵阵辣痛随着不见停下的掸子,越发带起了一跳一跳的钝痛。
“少,唔,少爷,我错了,啊!阿初额,错了!少爷饶……啊,饶了啊!”
直至荣升胳膊都酸了,这场似是无止的责打才算停下来,荣初早湿了眼眶,身体尚未适应方才的狂风暴雨,还在微微颤抖,荣升自己揉着发酸的胳膊却也未想这么轻易放过人,刚挨了一顿,想必也不敢再胡言了“说说吧,你最开始的想法。”
荣初一时有些张不开嘴,大口的喘了几口气才哽咽着张了嘴:“我,我动了心思,我想加入他们……”
这会儿是实话了,荣初不得不承认,夏跃春他们眼里的光很诱人,即使他明白这样的光像是一团火一般,入了便是飞蛾扑火,可是那一刻他还是动心了,他也想做一个为国效劳的爱国青年,他能辩的出他们的理想世界有多么的引人入胜。
“为什么?”荣升轻抚了荣初的背,为他顺一顺气。
“我知道,我欠了荣家很多东西,我了解,少爷待我有如亲弟,可是少爷,我也想为国效劳,他们所说的理念是让人向往的,那里的人,是人人平等的……少爷……我……”
荣升看着青年,却不由看出了几分苦涩,阿初长大了,却只能束缚在自己的家族使命中,这是不公平的,但他也绝对不能放他走,除了本属于荣升的家族使命,他身上还有四姨娘的期盼。
荣升又想起了妻子死前的模样,他能猜到筱蝶的确参与了什么他所不知道的组织,可他始终不了解,是什么能让妻子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,也要顶着身上的枪伤回家,只为了传达他所不知道的讯息,即使现在的阿初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也始终无法理解。
“there are two tragedies in life. the first is that you can't get what you want, and the second is that you can get what you want.(人生有兩個悲劇,第一是想得到的得不到,第二是想得到的得到了)”
荣升用一段英文打断了荣初逐渐不成句子的话,他将手上的掸子放回花瓶,“阿初,此时此刻,我宁愿你经历的是第一种悲剧。”
荣初此时的模样实际上是不适合谈话的,但是他又不得不保持这样的姿势去思考,他的腿已经失去了支撑,几乎全身的力气都压在了书桌上,胸口被压住的感觉,说话总是不舒服的,他挣扎着将胳膊支起来,腿脚重新用上了力气扯的身后一片刺头,可还没等撑的稍微高一些,荣升的手便按住了他的背,背上的伤被压的发痛,荣初识趣的只用手肘将自己撑起,经过这么一段折腾,他还是猜不透荣升的意思,他有些懊恼的开口,“阿初,阿初不明白,少爷。”
“我问你,革命是什么?”荣升的眼睛终于看向了一开始自己还在画的蝴蝶。
“是奋斗,是热血,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和家人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。”这是他今天下午听到的最多的话,荣初不假思索的便说出了口。
“或许……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吧,可是人活在世上总归会有对不起的人,对不起的事,会有必须要履行的责任,有无法放弃的执念。”荣升似是又一次看见筱蝶温柔的笑容,又一次看见她死前的决绝“若是革命会使你失去一切,你也觉得值得?”
“不,这是不冲突的,少爷。”荣初猛抬起头,想要去寻求和荣升的对视。
可是荣升没有看他,他的眼光死死的看着那幅蝴蝶“革命往往意味着血腥,暴力,意味着亲者痛仇者快,”他开始逐渐咬牙切齿起来,终于转头俯身看向了荣初“要是你在革命中失去了活着的权利,”荣升的呼吸又乱了“你要置你的干娘于何处,置我多年的教导于何处,置整个荣家的恩情于何处?”
荣初本已干涸的眼睛,又一次红了,他明白了,他永远无法去革命,至少在他还完荣家的恩情之前他是不配的,他忘了,他从来不是属于自己的。
“少爷,阿初……错了”
荣升拿起了方才荣初解下的皮带,将它在手中对折,点在了荣初身旁“五十下,今天的事情就算过去了,下来跪好,我要你一个承诺。”
荣初是怕的,但是如今比起怕他更多的,却是一份无法言说的委屈,一份肩膀上不得不承受的压力。他有些麻木的起身,拖着脚边的裤子,退后几步跪倒在地。
“啪!”
皮带无情的再度贴上已斑驳一片的臀部,随着荣初的痛呼,眼泪也跟着他的战栗掉在了地板上,荣升的手是不稳的,断断续续的抽打之下腰背臀腿几乎都受过波及,他强撑着身子受下了二十余记,终究还是被一记刁钻的角度抽打的想起扑倒,只有胳膊死死的撑住了身体。
“现在,我要你跟我说!”荣升又砸了几下,终于开口。
“是……”
“我荣初对天发誓。”
“我,荣初,啊!对天发誓。”五下落于背上。
“此生绝不参与党派之争。”
“此,此生绝不参与党派之争。”五下又将伤痕累累处重新点燃。
“若有违背。”
“若有违背!”又是五下落于腿后,荣初的身子狠狠一抽。
“将失我所爱,远我所敬,离我至亲。”
“少爷!”荣初重新直起了身子,泪眼朦胧,满是哀求。
“说!”毫不留情的几下将荣初再度抽低了身子。
“我荣初对天发誓,此生绝不参与党派之争,若有,若有违背,将失我所爱,远我所敬,离我……至亲!不敢违背!”
窗外的暴雨不知何时落下,一声巨雷惊响,烧断了电线,屋中骤然一片漆黑,巨大的闪电照亮屋中片刻,多余了色彩的蝴蝶油画,在雷电中一片扭曲。
那夜伦敦的雨远比今日下的猛烈,杨慕初看着和雅淑依依不舍的上了火车,荣升最后再看了一眼伞下人待着的地方,叹了一口气,本想逼阿初保住自己,快快乐乐的活一辈子,如今却是在这乱世中破了誓言。
人生有兩個悲劇,第一是想得到的得不到,第二是想得到的得到了,阿初如今你想得到的得到了,你终于走过了两种悲剧。
火车开走了,杨慕初终于走到了车站里,他低头看着心爱之人站过的地方,又看向火车开走的方向,他重重的跪倒在地,朝荣升磕了三个头。
他再度起身,拎起雨伞,却已面如死灰,荣升是他最敬重的人,和雅淑是他最爱的人,杨慕次是他最亲的亲人,一夜之间,他全部都失去了。最后连自己的身份也丢的一干二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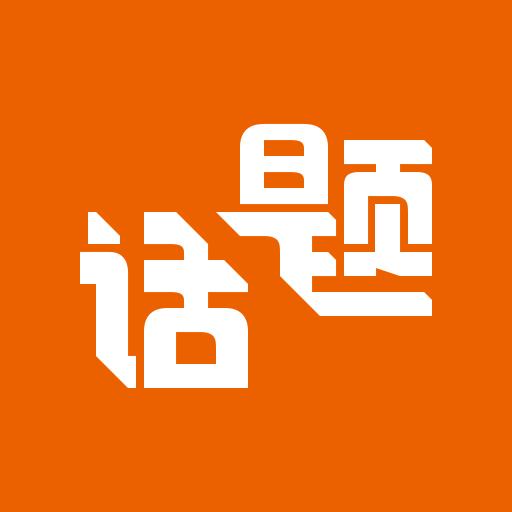


请登录之后再进行评论